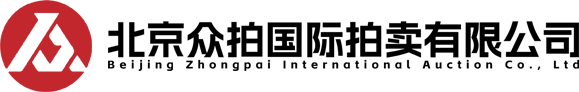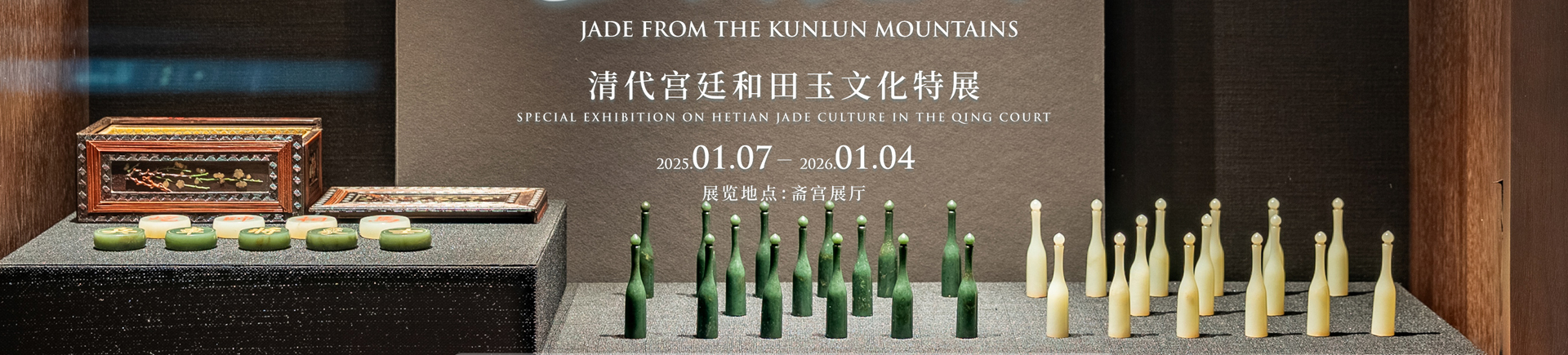拍品信息
拍品名称
元版元印 民间孤帙足本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(汉)何休注(唐)徐彦疏 陆德明音义
尺寸
26×16cm
估价
RMB 3,200,000-3,800,000
拍卖日期
2025-06-06
拍卖公司
中贸圣佳
拍卖专场
琳琅—重要中国书画及古籍夜场
拍卖会
中贸圣佳2025春季三十周年庆典拍卖会
著录
著录:1.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经部春秋P101
2.《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第06998号
3.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P311
拍品描述
元泰定致和间(1324-1328)刻本
2函28册 黄麻纸 线装
提要:半叶十行,行十七字,小字双行二十三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版心下有刻工“伯寿、仁甫、君美、善庆、以清、褆甫、王英玉、君锡、茂卿、余中、古月、应祥、文粲、王荣、安卿、寿甫、天易、以德、清远、丘文、善卿”等,均见于《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“监本附释音十三经注疏(元刊十行本)”。
参阅:《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》第二册P708
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,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,详情请见本图录《保税拍品竞买须知》。
元刻十行本是《春秋公羊注疏》最早版本,据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等著录,完本、残本存世共计十余部,但各馆对元十行本的著录,基本是“元刻明修本”,或者“元刻本”,有的还是“宋刻元明递修本”,并没有对元十行本的不同时期印本做出区分。北京大学张丽娟老师撰《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说》一文,对元十行本今存印本做了初步的调查梳理,认为今存元十行本传本中,未经修补的早印本非常稀见。
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间多次补版后印本,版心出现“正德六年、正德十二年”等纪年与“王世珍、陈景渊、罗栋、李红、叶廷芳、许成、詹积英”等刻工名,及誊写人名“廷器、廷器写”,和校勘人“怀浙胡校、闽何校、侯番刘校、侯吉刘校、府舒校、怀陈校”等,这在早印本中是没有的。
就《春秋公羊注疏》而言,目前所见的早印本国内外仅见三部:一、重庆图书馆藏本,夹杂数页宋刻本;二、南京图书馆藏残十卷本,收录于《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(第06998号);三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本。尤其卷八第十八页版心刻“致和元年”(1328),刻工“英玉”,为判断元十行本刊刻时间的重要证据。
元刻十行本群经注疏中,国图本《孝经注疏》有“泰定三年”(1326)的刊刻纪年,《论语注疏解经》《附释音周礼注疏》有“泰定四年”(1327)纪年。各经的原版刻工,也都互相交叉。说明元十行本各经刊刻时间相距不远,是由同一批刻工分工协作,先后相接完成的一套书版,刊刻时间应当就在元泰定、致和前后。
此外,张学谦先生撰文考证元十行本是官刻还是坊刻的问题,认为此本就是福州府学的刻本。通过对校可以看到,元十行本对宋十行本的文字也是非常忠实的翻刻,虽然说用了不少简体字、俗体字,也有一些翻刻误字,但整体翻刻还是严肃认真的,并不是后印本呈现出的错误连篇的情况。过去说元十行本有很多文字错误,其实很大原因是后印补版造成的。程苏东、张学谦等考证元十行本书版一直贮藏在福州府学,补版校订也出自福州府当地的官员,其刊刻出自福州府官方组织,当无疑义。
元刻元印十行本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
北京大学儒藏中心研究员 张丽娟
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经典,《十三经注疏》的版刻源流历来是版本学与经学文献研究的重中之重。而元十行本注疏作为明清以后通行《十三经注疏》的祖本、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的底本,在版本学、经学研究中具有超越其他经书版本的巨大影响力。同时,元十行本注疏又是前人认识非常混乱、面目很模糊的一个版本。一方面因为它和宋十行本的关系纠缠不清,另一方面它本身经过明代多次补版递修,现存印本纷繁复杂,学者难以见到元十行本初始面貌,有关它的刊刻时间与刊刻性质也存在种种模糊认识。元十行本注疏现存印本并不鲜见,但绝大多数是经过明代历次修补的印本,完整流传、未经修补的早印本十分罕见,全部十三经中仅有可数的几部传存。本次中贸圣佳拍卖本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二十八卷全本,原版清晰,未经任何补版或局部修整,能够反映元十行本初始面貌,是今存元十行本传本中一部难得的元刻元印本。
一、元十行本注疏的刊刻时地
我国的经书注疏合刻本,主要有八行本与十行本两大系统。八行本陆续刊于南宋高宗至宁宗时期,后代未再翻刻,流传罕见,民国以后方有影刻及影印本。十行本约刊于南宋中期,经元代翻刻,明清时期递相校订重刊,影响至今。长期以来,学界所能利用的《十三经注疏》版本,包括元刻明修十行本、明嘉靖李元阳本、明万历北监本、明崇祯汲古阁本、清乾隆武英殿本、清嘉庆阮元本,及今日常用的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本等,都属于十行本一系。作为明清以来通行注疏合刻本的祖本,元十行本的地位与影响不言而喻,有关元十行本的版刻与校勘问题,也始终是聚讼纷纭、引人瞩目的议题。
元十行本乃由宋十行本翻刻而来,长期以来被误认为宋刻,前人书目著录中的所谓宋十行本注疏,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元十行本,且绝大多数是元刻明修本。阮元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以元刻明修十行本为底本校勘群经,而称“宋十行本”;南昌府学以元刻明修十行本为底本重刊《十三经注疏》,而称“重刻宋本”。实际上,真正的宋十行本今存只有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谷梁》三经,及刚刚在古籍普查中发现的数叶《公羊》零叶而已。而完整传存、未经补版的元刻元印十行本,亦十分罕见。目前所知,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《孝经注疏》、《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》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附释音尚书注疏》、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《周易兼义》、重庆图书馆藏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等有数的几部。其中《孝经注疏》有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本,《周易兼义》有《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》影印本,《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》有国图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发布全文影像。1
国图本《孝经注疏》有“泰定三年”(1326)的刊刻纪年,重图馆藏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有“致和元年”(1328)纪年,这都是初印本上出现的纪年,是刊刻年代的铁证。此外,《论语注疏解经》《附释音周礼注疏》有“泰定四年”(1327)纪年,见于原版叶。各经的原版刻工互相交叉,出自同一批工人。这说明元十行本各经刊刻时间相距不远,是由同一批刻工分工协作,先后相接,完成的一套书版,整体刊刻时间当在泰定、致和前后。其刊刻风格属典型的建本,刻工亦多见于元代福建地区刻书,近年张学谦根据多方面资料考证,认为元十行本当为福州路官府所刻。2从今存元十行本早印本情况看,各本皆版式齐整,刻印不苟,纸墨亦相当精良,并非常见的后印本所呈现的邋遢样貌。元十行本书板长期存于福州府学,明代经福建当地官员修补校勘,故出自官刻的可能性极大。
二、今存元十行本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诸印本
元十行本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今存印本亦不尠见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南京图书馆藏一部“元刻本”,又“元刻明修本”若干。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、日本静嘉堂文库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、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等亦有收藏。影印本有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藏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《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》影印柏克莱藏本。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天一阁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及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本有网络全文影像发布。笔者曾调查元十行本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的补版递修情况,并将今存印本划分为如下几期:3
1.元刻元印本
重庆图书馆藏本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原著录作“元刻明修本”,2019年笔者参与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期间,确认此本为未经修补的元刻元印本,并发现其中有配补的宋十行本版叶。4此结论已为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采纳(第12347号)。南京图书馆藏本,从《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收录卷五首叶书影看,当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所著录,为未经修补的早印本,惜仅存十卷。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一部(索书号106.22 00651),其版面较为漫漶,又多缺叶,不过尚未见明前期补版,印刷时间或在元末明初时期。
元刻元印本皆原版,版刻形式齐整,版心皆白口,上刻大小字数,下有刻工姓名。卷八第18叶版心刻“致和元年”(1328),刻工“英玉”,为判断元十行本刊刻时间的重要证据。
2.明正德十二年补版印本
日本静嘉堂藏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为此期印本。其卷四第11-12叶为明前期补版,正德补版版心经剜纸,参照北京市文物局本可知卷九第1-2叶为正德六年补版,写工“李红誊”,刻工吴郎;卷六第7-8叶、卷十二第3-4叶等为正德十二年补版,刻工余富、杨尚旦。卷一第7-8叶版片中部为横贯的大断版,尚未经修补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本(索书号03289)亦有正德六年、正德十二年补版,卷一第7-8叶断版处已经局部镶补,但此本较静嘉堂本保存了更多原版,或有不同印本之配补。
3.明正德末嘉靖初补版印本
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两部印本(索书号106.22 00650及106.22 00652)属此。与静嘉堂本相较,其明前期、明正德六年、正德十二年补版大体一致,卷一第7-8叶断版处已经局部镶补,卷二十五各叶下端经局部补刻,卷二十八第13-14叶经大面积修补,第15叶则为新增补版。但尚未经嘉靖大规模补版。
4.明嘉靖补版印本
北京市文物局藏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天一阁藏本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、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等属此。除上述明前期、明正德补版外,增入大量嘉靖新补版,版心有“侯吉刘校”、“林重校讫”“运司蔡重校”等校勘人名,刻工有叶再友、江盛、陈珪、王进富、蔡蓬头等。原版及明前期、明正德补版叶多经局部修整改刻,并有文字校订。
三、中贸圣佳本与诸印本之比较
以中贸圣佳拍卖本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与今存诸印本比较,可得如下认识:
1.此本为元十行本注疏中难得的元刻元印本。全本字迹清晰,版面整洁,印制精美,未见任何补版及局部修补痕迹。各叶版刻形式规范统一,版心上刻大小字数,下有刻工姓名,包括伯寿、君美、以清、善庆、仁甫、禔甫、王英玉、君锡、君善、余中、古月、应祥、文粲、王荣、安卿、德远、寿甫、天锡、以德、丘文、善卿、德甫等人。卷八第18葉版心刻“致和元年”(1328),刻工“英玉”,为元十行本刊刻年代的有力证据。
2.此本上、下两函乃由两个不同印本配补而成。上函卷一至十三,印刷时间更早,仅偶见断板,卷一第7-8叶局部断裂,与重庆图书馆藏早印本一致,印刷时间或较重图本稍晚。下函卷十四至二十八,部分叶面可见底部磨损情况,不过整体仍字迹清晰,远在台图藏早印本(索书号106.22 00651)之前。静嘉堂本、文物局本等中期、后期印本中的明代历次补刻版叶,此本皆为清晰的原版。无论上函、下函,在今存元十行本诸印本中皆可称上乘之品。
3.内容完整。今存元十行本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印刷较早之本,往往多见缺卷或缺叶。如南京图书馆藏早印本仅存十卷;重庆图书馆藏早印本亦有缺叶,除有宋十行本配补叶外,另有数叶为后人抄补甚至仿刻;台图藏早印本(索书号106.22 00651)有多卷抄配,存卷中亦多有缺叶。至于静嘉堂本、文物局本等,其中明代补刻版叶渐续增多,更难以反映元十行本完整面貌。
4.保存元十行本初始文字,可正后印本讹误。以卷四第11-12叶为例,此二叶重图本、中贸圣佳本皆为原版,中贸圣佳本有断板,但文字仍清晰。台图藏早印本(索书号106.22 00651)此二叶缺叶,其印刷时书板或已遗失,或已严重损坏。至静嘉堂本、文物局本等,此二叶皆已替换为明前期补版,文字多见讹误。如第11叶上半面第5行疏文“故《礼运》道三皇时云”,“运道”二字重图本清晰,此本稍有残损,静嘉堂本、文物局本等后印本遂误作“进退”。第7行疏文“又下《系辞》云”,重图本与此本“下”字皆清晰,静嘉堂本误作“不”,文物局本改作“易”。此盖明前期补版时误“下”为“不”,嘉靖校订中发现“不”字文意不通,遂剜改作“易”,亦误。第11叶下半面第10行注文“中心死疾鲜潔”, “潔”重图本与此本皆清晰,静嘉堂本、文物局本误作“屑”。第12叶上半面第4行疏文“则知此皆堂上豆数也”,重图本清晰,此本“皆”字在断板处,上半稍有残损,静嘉堂本、文物局本遂误作“者”。以上诸例,此本与重图本文字皆一致,可正后印本讹误。由此本更可见后印本致误之由、讹变之迹。
注:
1 参见笔者《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说》,载《岭南学报》复刊第十七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。《国图藏元刻十行本<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>》,载《国学茶座》第十一期,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。
2 张学谦《元明时代的福州与十行本注疏之刊修》,载《历史文献研究》总第四十五辑,广陵书社2020年。
3 《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说》。
4 《记新发现的宋十行本<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>零叶——兼记重庆图书馆藏元刻元印十行本<公羊>》,载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,2020年第4期。